中国摄影排行榜系列访谈丨李舸:我要表达的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

小编注:日前,由丽水摄影博物馆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已正式发布。为了对本届上榜艺术家作品和创作背景作更多了解,主办方邀请相关业内人士对所有上榜者作了系列访谈,陆续分期刊出。

采访人:吴栋
吴栋,写作者、编辑、评论人,专注摄影与影像领域,现任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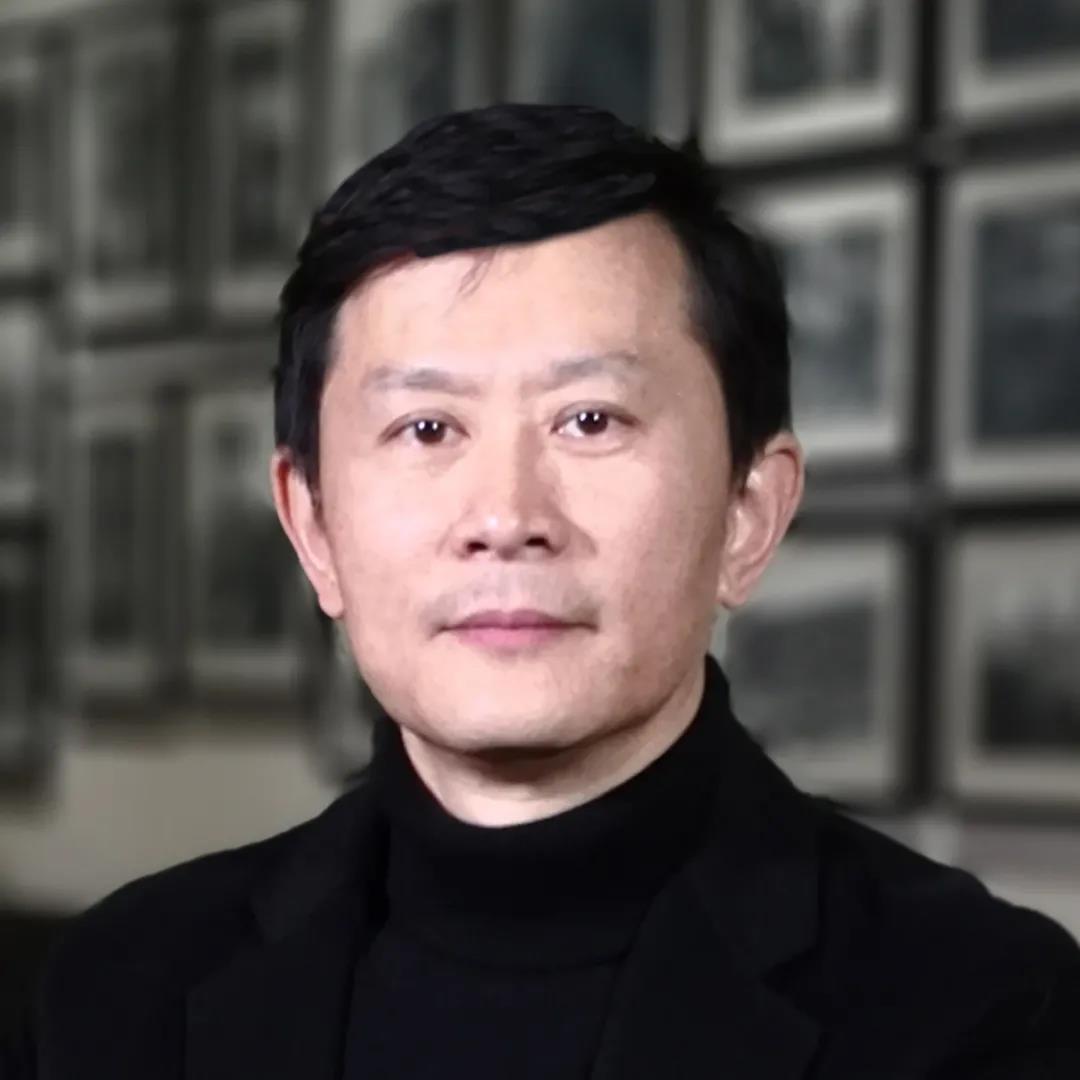
艺术家:李舸
李舸,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获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奥运会体育摄影作品金质收藏大奖等。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中央国家机关优秀专业技术能手”、 “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人民日报 “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
导语:事实上,在看到《你是我最牵挂的人》这组作品时,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到一年多前疫情汹涌的状态。对于这场疫情,我的感受大多来自于媒体,微博、朋友圈、各大平台……媒体左右着人的喜怒哀乐,而实际上,没有亲临现场的人是永远无法感受到现场的氛围的。
在疫情走向还无从预测时,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李舸与其它四位摄影师——刘宇、柴选、陈黎明、曹旭,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他们发回了前方的报道,并且动员近200位摄影师,为援鄂的4.2万余医护人员每人拍摄了一张肖像。在此期间,李舸发现许多医护人员都珍藏着他们与患者的合影和救治时的工作照,有感于医护人员和患者间在非常时期的亲密关系,李舸继而拍摄了项目《你是我最牵挂的人》,拍下了医护人员向镜头展示自己手机里珍贵照片的肖像。

△ 福建省立医院护师徐健
吴:时隔一年多,您对当时的现场体会还强烈吗?
李:依然是很强烈的,因为我们是亲历者,在那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种经历跟我之前的所有采访都不一样,虽然近30年来我在一线采访过许多重大突发性事件,但没有一次耗时如此之久,投入如此之深。
吴:您带了5个人的团队去武汉。在那,你们组织拍了4万多位医护人员的肖像和用于前方报道的照片,后来您又拍了《你是我最牵挂的人》。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照片间的区别的?有没有分职务作品和个人想要拍的?
李:当时中国摄协组成五人赴湖北抗击疫情小分队前往武汉,到达后又集结了已经在武汉进行采访的各媒体记者与志愿者们共一百余位。此行经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领导批准,得到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大力支持,我们都是自愿去的,没有人预想过在那个环境下能拍摄到4万多人的肖像。我们觉得这是留给国家的一笔珍贵的影像文献档案,这跟摄影师个人名利无关。

△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护师施琦
吴:您当时倡导过摄影人要居家。然后您自己就去武汉了。当时好像听到些质疑的声音说:“您提倡居家,自己却去了。”您怎么看待?
李:这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呼吁居家的对象是没有工作职能的摄影人和摄影爱好者们。当时春节期间,很多人还是想出门旅游、拍摄,所以我们才希望大家尽量居家不外出,全力支持国家抗疫。倡议书里也写道,大家可以在家中,记录身边的情况与变化。实际后来也有很多人拍出了他们身边感人的抗疫故事。
而我们是摄影记者,去一线采访是工作职能。就我个人而言,从业30年来,遇到洪灾、“非典”、地震、大火等这些重大突发灾难,我都第一时间去往现场进行采访拍摄的。摄影记者与其他摄影人或者爱好者是有些不一样的。
吴:你们在武汉的作息大概是怎样的?
李:刚到时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觉,我们没有经过防疫培训,虽然我也经历过很多生死,但全然不像这次,时刻会担心自己被感染。武汉的冬天很冷,北方人不太习惯,我们住的旅馆条件也不好,不敢开空调,更没有服务员。
我每天晚上回到旅馆整理照片、发稿,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钟才能休息。躺下后根本睡不着,满脑子都在想第二天要去拍什么。当时在武汉,我就想尽可能多地去记录,所以天一亮就赶紧出门拍摄。我们是最后一批从武汉撤离的记者,那段时间虽然艰难、辛苦,但现在回看,是很有必要的。

△ 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护师蔡小珍
吴:我看您拍的照片,有一些简易的照明,您现场搭建的方案是怎么考虑的?
李:我们当时从决定到出发,只有半天时间,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前期一大批照片都是利用现场自然光拍摄的,从病房里出来的过道很窄,如果搭一些大型灯光设备会影响医护正常的工作。随着我们这次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武汉的一些志愿者借了我们些便携式LED灯,后来又买了一套。所以后期我们在拍摄时基本就靠一个主光源、一个辅光源提供照明,这种小型移动设备能起到辅助作用。
吴:您是在怎样的场合拍下医务人员的照片?
李:我们在拍摄医护人员之前定了两个基本原则,拍摄绝对不能影响病区正常的救治和护理,以及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
当时我们刚去的时候,条件很简陋,防护物资供应也很紧张,好多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接班的时候不吃饭、不喝水,这样几个小时的工作可以不上厕所,就是为了省出一套防护服。我们守在缓冲区淋浴间门口,等医护人员下班走出病房,就在进淋浴间前扔掉口罩的一瞬间进行拍摄。另外,值班医生中午或晚上要在缓冲区的休息室吃饭,那时我们也会给他们拍照。为每位医护人员拍摄大概也就短短一分多钟,真正摘下口罩拍摄大概就几十秒钟吧。

△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护师孔娅娅
吴:您的照片里,医护人员都拿着手机。手机里的图像让我联想到了医患关系,此外也是个额外的信息点。为何您会设置手机这个元素呢?
李:有人认为手机只是个道具,是外在形式。实际上,我更在意手机在那时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从历史的跨度中去看这次抗疫,手机的价值非常独特。
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我当时申请进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定点病房采访了十几天,我用发生在身边的两个小故事,侧面回答一下为什么要加入手机这个元素。
第一个故事, 2003年5月8日是北京“非典”定点医院正式启用的第一天,患者从市内各个医院转来,他们携带的所有物品都属于污染品,包括纸质的病例,都不能拿到非污染区。那问题来了,看不到病例,清洁区的专家怎么会诊?当时的解决办法是让污染区里的医护人员把病例贴在隔离的玻璃窗上,然后非污染区的医生在玻璃窗的另一侧,拿一张白纸把病历上所有的文字和图像全部抄一遍,再把拷贝版送给专家。我当时就拍过这样的照片,这种情形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另一个故事,我当时所在的病区有个住院的老奶奶,她的老伴病得很重,住在我们楼下重症监护室。那时规定很严,不同病区的所有人员是不能交流的,两位老人互相的牵挂怎么解决?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病房里也没有台式电话,医务人员就想了个办法 —— 让两个人写信,通过电梯上下传递。两个病区的护士每次事先用对讲机沟通好,让老奶奶写个纸条,我们病区的护士把它放到电梯里,无人的电梯下到重症监护病区, ICU护士把纸条拿出来消毒,再给老爷爷看。老爷爷写好纸条,再由护士放在电梯里升上去,每一步都很费劲。
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们病区的护士长在老奶奶门口徘徊,她说老爷爷昨天晚上去世了,她拿着老爷爷去世前的绝笔,要交给老奶奶。后来我没跟着进去,因为那一刻,道德和礼貌远比拍到所谓的“有冲击力”照片更重要。
这次在新冠肺炎病房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患者住院是没有亲人陪伴的。我发现患者们只要意识清醒或行动自如,手里都会紧紧握着手机。此时,手机已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就是他的家人、就是彼此的牵挂,是一种心理安慰。我们都知道,目前为止治疗新冠还没有特效药,那么在这个特别的状况下,对患者的心理疏导非常重要,手机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特殊的“精神良药”。
在这次的拍摄交流中,有些医护人员会举着手机给我们看他们和患者的合照。当时我觉得挺奇怪:怎么几乎每个人手机里都有这样的照片,他们哪有时间拍照呢?后来他们说,手机里大一部分照片都是患者拍的传的。有些医护人员在回到自己驻地的时候,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继续通过微信与患者们进行沟通,做心理疏导,很多康复的患者在出院前也会要求与医护人员合影。

△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护师马静宇
吴:《你是我最牵挂的人》在网上展出的是一些彩色照片,但我看了一些展览现场,包括时代美术馆里展出的时候,它是黑白的。您怎么看照片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展示效果?
李:彩色的是当时作为新闻照片发稿的。但沉淀下来后,我要思考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表达时,内心更倾向黑白照片。首先是想把有些不必要的色彩过滤掉;其次,黑白也更加肃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场灾难,我要表达的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
 《你是我最牵挂的人》展览现场
《你是我最牵挂的人》展览现场
吴:您后来和医护人员们还有联系吗?
李:有些依然保持着联系。2020年12月底,我们做过一次回访,当时有三名医护人员回到武汉寻访他们曾经救助过的患者。其中有一名护士曾参与护理过98岁的天文学泰斗 —— 韩天芑,他当时是高龄重症患者,曾经几度抢救,最终康复出院。我跟着这位来自福建的护士去韩老家,老人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身体很健康。当他第一眼看到护士时,眼泪夺眶而出。韩老说,当时在病房中,只能看到医护人员的眼睛,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貌,也不曾想到她会是第一个从外地赶来回访的医护人员。这感人的一幕被我们记录了下来,还做了一条专题片。

△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师吴映霖
吴:那么多年,您拍过很多重大事件,在大型灾难面前,一个摄影师可能既要有非常强大的抗压能力,也要有一种同情心。不知道您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怎样?在紧张压抑的环境下,您是如何自我调节的?
李:我这个人心态比较好,始终都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生死了,包括这次武汉,如果心理不强大,我是不可能带队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是媒体记者,一直在一线采访,也慢慢形成了属于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你说到拍摄的同情心,我们在武汉期间每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最多一天能拍一百多位医护人员,这里面有近3/4的人都会在镜头前流泪。给他们录视频时一般都是问一句话:“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干什么?”或者是:“你最牵挂的人是谁?”。我们只要一问,他们就会流泪,我也会跟着流泪。我们也跟一些康复的患者保持联系,除了拍他们,我们还拍社区干部,拍普通市民,同样从他们身上收获很多感动。尤其是那些社区干部,家中老人孩子没法照顾、家人的生活物资也保证不了,但他们就这样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去,所有这些都在感动着我。
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过不去的坎,要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信念。在这些重大突发事件前,你能不能挺起身来把事情顶住,这很重要。